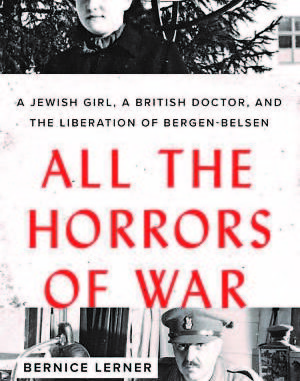
蓓妮絲·勒納在2020年出版的《二戰悲慘境遇》。(courtesy)
英國辛德勒的精彩救援故事
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,歡迎轉載,請註明出處
編譯:台灣ICEJ團隊
新聞出處:TOI|新聞日期:2020/4/17
就在75年前的當週「1945年4月第三週」
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內「斑疹傷寒」遭逢敵手
最近出版的《二戰悲慘境遇》(All the Horrors of War)一書中提到
在德國境內解放納粹「恐怖集中營」後
英國旅長格林·休斯(H. L. Glyn Hughes)
想要在集中營內盡可能拯救更多性命

1945年在德國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的最後一間房舍進行焚燒儀式。(public domain)
德國貝爾根-貝爾森(Bergen-Belsen)—當盟軍第一批醫官抵達所謂的貝爾根-貝爾森「恐怖集中營」後的幾天內,英國旅長格林·休斯便打算在當地蓋一間歐洲最大的醫院。
為了對抗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內的斑疹傷寒和飢餓問題,這位英國軍官在他計劃中採取了相當不尋常的判別標準,包括死亡率、墳塚數和受斑疹傷寒感染的營區數。英國軍官休斯曾多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獲頒勳章,現在他每天被迫判定他人生與死。
《二戰悲慘境遇:猶太女孩、英國大夫與貝爾根-貝爾森的解放故事》(All the Horrors of War: A Jewish Girl, a British Doctor, and the Liberation of Bergen-Belsen)一書的作者蓓妮絲·勒納(Bernice Lerner),在書中交互陳述休斯的英勇事蹟與她母親的故事,她母親也是這名軍官釋放的其中一名囚犯。
15歲的芮秋·杰紐斯(Rachel Genuth)是勒納的母親,當年被人從奧斯威辛(Auschwitz)送到貝爾根-貝爾森,正逢貝爾森最致命的時刻。這間為4千名囚犯建造的集中營,頓時多了6萬名罹難者,多數都是猶太人。
1945年的初春時節,上千具屍體就堆在集中營外,這樣的噩耗是從集中營惡劣的衛生條件下揭開序幕,最後由斑疹傷寒負責收尾。上一個冬天,在集中營內就有3萬5千人喪命,其中包括安妮(Anne Frank)和瑪歌·法蘭克(Margot Frank)。
勒納在書中寫道:「芮秋明白,當囚監(被納粹黨衛軍委以管理之責的犯人)拿著喝起來像洗碗水的湯出現時,只有體力足夠支撐的囚犯能拿到一點湯喝。許多人會推擠、踐踏這些身體羸弱多病的囚犯,但只要有人走出隊伍就會被活活打死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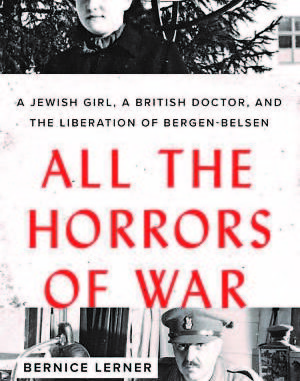
蓓妮絲·勒納在2020年出版的《二戰悲慘境遇》。(courtesy)
1945年初,在運送囚犯途中將斑疹傷寒帶入集中營內,病患會出現紫色斑點、頭痛和意識不清。這種斑疹傷寒在饑荒和戰爭時期最為致命,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內的囚犯就成了「斑疹傷寒熱」 (Typhus Fever)最容易下手的目標。
休斯跟著英軍才剛抵達集中營,就被迫要立即決定優先救治的病患。此外,屍體只能四處堆放,還有6萬名倖存者需要緊急醫療處置。勒納寫道:「休斯的計劃著重在將囚犯區分為三大類,包括最有可能存活,最可能病逝,還有處於生死交關,需要立即救治的病患。」休斯跟著英軍才剛抵達集中營,就被迫要立即決定優先救治的病患以做最適當的醫療隔離分流處置。此外,除了隨處可見的屍體外,還有6萬名倖存者需要緊急醫療處置。勒納寫道:「休斯的計劃著重在將囚犯區分為三大類,包括最有可能存活,最可能病逝,還有處於生死交關,需要立即救治的病患。」
生產線式醫療
勒納寫道,在軍隊人員和97名英國醫學系學生的協助下,休斯每天要處理的死亡人數多達數百人,遠超過集中營4月15日解放當天的死亡人數。他要醫官進到每個營區內進行「快速判定」。
「休斯的計劃著重在將囚犯區分為三大類,包括最有可能存活,最可能病逝,還有處於生死交關,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。」
勒納是波士頓大學「品格與社會責任中心」(Center for Character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)的資深學者,她寫道:「撤退後若接受基本照護,是否能提高這個人的存活率?救治工作就是按照這個原則進行。」

解放後不久的德國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。(public domain)
勒納的母親看著朋友死於斑疹傷寒,在軍營內又被其他囚犯毆打,幾乎要死;她又染上了肺炎,這個疾病影響她往後幾十年的健康。
「芮秋學到讓人不忍卒睹的例行公事:每天早上空卡車會一車車開到女性集中營,收集這些囚犯抬出並堆放在營外的屍體,接著脫去她們身上的衣物。」
「想要為他們做點什麼」
雖然勒納的母親從未看過休斯,透過她女兒的研究,她更瞭解這人的事蹟,以及她獲救的詳細經過。
在勒納投身寫作這本書的十年間,她能夠向現年90歲的母親詢問許多細節。因此作者得以勾勒出她母親家族在二次大戰前的詳細樣貌,並追蹤其他親人的下落。

作者 蓓妮絲·勒納 (courtesy)
勒納遠渡重洋,來到大西洋彼岸,與休斯1973年過世前認識他的人進行訪談。從各方面來看,因為休斯在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的英勇事蹟,人稱他是英國的「奧斯卡·辛德勒」(Oskar Schindler),是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。
當問到休斯為了終止疫情,在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採取的措施時,勒納指出了英國軍隊的募兵情況。勒納表示:「英軍治軍嚴明且反應迅速;但在面對休斯的情況時,卻未能盡速反應,或即時補足人力。」休斯設立的醫院,成了歐洲最大的醫院。休斯負責監督工作,替曾為階下囚的1萬3千名倖存者提供照護。勒納表示:「他是在跟時間賽跑。」休斯採取的果斷行動,包括讓英軍控制集中營附近的醫院,請德國病患將床位讓給這些集中營受難者。他也要求德國當地的領導幹部「參觀」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,讓數百位幹部被迫見證他們下令執行的成果。

在德國貝爾根-貝爾森田野上的紀念墓碑。
(攝於2019年11月28日)(Matt Lebovic/The Times of Israel)
休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表示:「人類經歷這樣慘絕人寰的對待,貝爾森絕對佔有獨特位置,這在人類史上可謂空前絕後。在惡名昭彰的行徑下,這些受難者被降格為非人的存在。」但還是有少數幾位厭戰的有志之士,想要救起能夠救治的人,想減輕他們的痛苦,並讓他們在痛苦深淵中獲得平靜。

英國旅長格林·休斯。(public domain)
勒納表示,休斯做事「講求方法和工廠式效率」,知道要將資源運用到極限,把DDT化學藥劑噴灑在衣服的每個角落,以消除集中營內的斑疹傷寒和其他疾病。勒納表示:「接著他將整個營區都燒掉。」
勒納寫道:「休斯下令要軍中攝影師捕捉第47營的畫面;希特勒肖像在烈火中燃燒,休斯正與同事交談,身後瀰漫著煙霧;升起的英國國旗在戲劇性場景中飄揚。
永無止境的奮鬥
二次大戰結束後,休斯仍持續為人們的性命和尊嚴奮鬥。在訪查數百間醫院和療養院後,他寫下了《臨終前的平靜:英國安寧照護調查》這份頗具影響力的報告。
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,休斯抱怨照護病患和老年人口的資源不足。他敦促政府應為照護體系大幅提供資金,這些照護機構通常需要仰賴宗教團體和志工的支持。過程中,他協助促成了英國國民醫療保健服務(National Health Service)的創立。

大型墳塚內有1萬名罹難者,屍首在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解放期間仍未安葬
(攝於2019年11月28日)(Matt Lebovic/The Times of Israel)
勒納寫道,在生命的最後階段,這些臨終病人需要覺得「有安全感、不孤單,有人在乎他們,且有人願意為他們做點什麼」。
勒納表示:「休斯真的有同理心,他將這些受難者當作人看待。」這位作者補充道,不是每位英國軍官對待這些猶太大屠殺倖存者,都如此崇尚人道精神。
勒納寫道:「休斯將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裡的每位倖存者,當成是他親身拯救的對象。雖然無法阻止成千上萬的人死去,沒有人的生命該如此終結。但在集中營解放後十五年,他擁抱機會,為臨終病患提供了人道對待的做法。」

於1945年4月拍攝貝爾根-貝爾森集中營內的受難者。(public domain)




